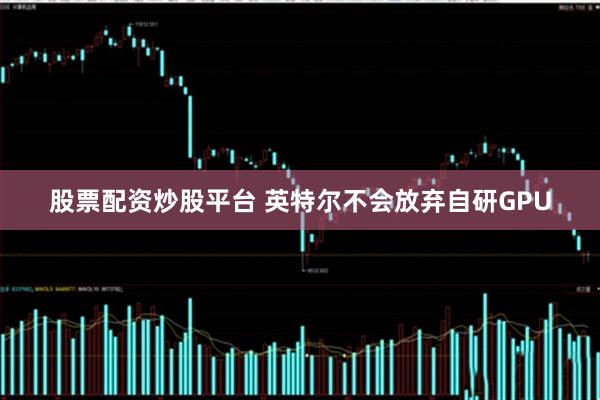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大山深处,世居着一个古老族群——白马藏族,他们是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之一,被称为“人类活化石”。在那个没有文字、只有时间的部族,当镜头穿越1999年到2024年,穿过外面世界的沧海桑田去凝望同一片土地、同一群人股票配资炒股平台,会是怎样的生命之歌?

10月31日晚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携纪录片《白马姐妹》来到大光明电影院,带着遥远的传说、沧桑的民族故事。影片将于11月5日登陆全国艺术联盟专线发行。如映后环节张同道所言,“我的镜头不撒谎”,这部纪录片里有能歌善舞四姐妹的生活变迁,有一方村寨遭受百年洪水后的韧性重建,也有一个古老部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、坚守与困惑。
简言之,《白马姐妹》用影像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族群留下一段真实的生命印迹。

“爷爷的爸爸是谁?”
《白马姐妹》并非第一部关于白马藏族的纪录片,早在2004年,央视就播出过一部《白马四姐妹》。特别的是,两部背后的主导是同一位纪录片人。
1999年,张同道作为央视《中国文化之谜》的导演之一,正在四川找寻三星堆的答案。他们顺着长江往上游寻,一路找进深山,却意外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厄哩寨见到了山林里的白马人。留下三星堆文明的族群不知去向,而眼前这群鲜活的白马人却源头成谜——因为没有文字,没有记载,关于这个族群的发源、流变、迁徙,至今没有学术上的定论。今人只知,他们主要聚居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、阿坝州九寨沟县以及甘肃文县等地,2015年人口约2万余。
“因为没文字,没记载所有人的记忆,到爷爷就没有了,爷爷的爸爸是谁?暂时没有答案。”来自纪录片人的敏感和职责让张同道意识到,要记录,就是此刻。

随后的过程似乎水到渠成,一个能歌善舞的部族,像花儿般鲜活的伍音早、晓小、小英美和金银早四姐妹进入张同道团队的视野。“与其说是我们选择镜头聚焦的方向,不如说,是被记录的人们自然生长。”
不过,如今再回望,张同道坦言,最初的镜头是带着距离感的。他和小英美对话,问一长句,对方答几个字,表情也始终没什么波澜。小英美的父亲更是只露出了一个背影。1999年的初次拍摄告一段落,临别时张同道说下次还来,“老人是当过兵的,见过世面的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,流露出充分的不信任,只是他没有说破”。
直到第二年夏天,这群纪录片人又扛着机器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走进厄哩,一见面,老爷子用双手抱住张同道的手说了句“你说话算数的”。
就这样,一个承诺,纪录片人践行了四年。1999年到2003年四年时间,他们与白马人同吃同住,记录下四姐妹的成长、她们改建家庭旅馆的生活场景,见证当地从伐木狩猎转型发展旅游业;也融入一些白马藏族的历史传说与文化细节,比如“跳曹盖”这一国家级非遗。2004年,纪录片《白马四姐妹》在央视播出,还入选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。
但“爷爷的爸爸是谁”,这个问题依然等待答案。
命运的齿轮在2020年盛夏再次转动。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冲毁白马村寨,二姐晓小的女儿田冬梅一通带着哭腔的电话“我妈妈已经不见三天了”,把张同道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神秘的村寨。他带着团队重返故地,又是四年。
“五块钱一个镜头?”
一个村寨,此前已用四年时间拍摄记录,2020年,同一片土地,同一群人,还能拍什么?
固然,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,成了最强力的“编剧”,生生给纪录片开辟出重建家园的“剧本”。但时间本身的力量其实已足够动人。上海观影现场,复旦大学教授唐骏感慨,时间是纪录片的首要因素,“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,所有故事的张力、情感的积淀都会呈现出来,而生活本身比戏剧更精彩,所以可以说时间是纪录片最好的编剧”。
时间在《白马姐妹》里首先显影为记录载体的变迁。从1999年、2000年胶片记录的4:3画幅,到2020年后数字摄像机甚至手机留下的16:9横屏、竖屏不一的画面。
更有意思的变化,在乎镜头的距离感。
张同道提及,1999年,他第一次拍摄白马人,听闻他们即将在除夕那天晚上狂欢一夜,“全寨子人要唱跳一晚上,我就从峨眉电影厂拉了一卡车的灯、带着大摇臂进山”。他想把整场仪式记录下来,费劲力气,结果发现,现场电力只够支撑两个摇臂……“镜头与人是有距离的”。
四年又四年,纪录片团队几乎跑遍厄哩寨全部100多户人家。渐渐地,人与镜头之间的距离感,也在时间的推移中步步消弭。
要记录口口相传的民歌,张同道把村寨里“70后”“80后”乃至“90后”都“摇”来了。想拍摄村寨里大会小集,村民们也毫不设防,成片里一些镜头都快“怼脸”了,都无人叫停。
完全真实、敞开的拍摄里,《白马姐妹》获得了许多可遇不可求,更无法摆拍的镜头。比如,有村民站在山路边,半真半打趣地对着镜头说:“拍一下五块钱。”张同道说,当然不可能给钱,“给钱了,他们就是我的演员了”,纪录片追求的,不介入、不审视、不评判,仅仅真实记录当时的状态。

又比如,灾后重建的过程在贴地视角里重现。特大洪水过后,大地一片狼藉,村寨面目全非,摄制组在洪水过境后一周内赶到当地,紧随村民重建的脚步,在泥泞中记录真实。重建的过程有众志成城的一刻。古老的木质房在山地里平移,没有任何现代机械助力,纯靠村民们肩并肩、手靠着手,跟着齐整的号子一步一步,稍有不慎,二层的房梁脱落掉下,虽是木质,也能砸出脑门上一个包、渗出血。这样的互帮扶持,村民们不谈钱,一声招呼、一呼百应,主家只需架锅下厨,杀鸡烹肉,让乡亲们饱餐一顿。
当然,艰辛劳作是必然,还有更让人着恼的事。政府给村里的重建和维护发放了一定金额补助金,100多户人家,重灾、轻灾如何界定,村寨的公共设施该不该从这笔补助金里切块,都成了村大会上据理力争的矛盾焦点……

这些情节不预设、不粉饰,更不造假,那是白马人发自内心的情感释放,而合乎人性本质的真实流露,也能让观众轻易共鸣。
“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分享给各位。我们唯一的差距是事情发生时,我在场而你们不在场,这个民族我遇见过,而大家可能没见过。”张同道说,团队花时间记录,就是想把一个群体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生活分享给大家,如此而已。
“生命如旅人,不唱不跳干啥”
高清的4K画面里,白马神山峻伟神秘,王朗雪岭巍峨挺拔,夺博河水奔流不息,大熊猫等多种珍稀动物就在村寨不远处的国家公园里安然栖息——一切看起来,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但新建的高速公路让外面的世界不再遥不可及,现代化进程无可避免影响着也改变着古老村寨农耕播种、狩猎伐木的原始生活方式。
如何传承着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握手言和,白马人自有智慧。《白马姐妹》记下他们在KTV的一夜,不似1999年整个村寨围着篝火唱跳一整夜,搬进县城的楼房后,村民们有时家中载歌载舞到深夜,扰得邻居报警。到KTV里唱一夜、跳一夜,是白马人找到的折中方案。

更有意思的变与不变,投射在白马四姐妹的生活里。1999年春节,除了二姐晓小,其他三姐妹都一心想往外跑。时年25岁的大姐伍音早,想逃却留下;三姐小英美当年17岁,站在成年的当口立志,“我要去九寨沟跳舞”;四姐金银早才13岁,说话奶凶奶凶地:“我不喜欢大山,我要出去!”
到了2020年夏天,一场灾难又将姐妹重新聚拢,共同投身于白马寨的重建中。如果说白马姐妹年少的出走是金花盛开的坚然决心,那么成长后的回家便是属于白马寨人的回归。而张同道带着团队用镜头完成的,则是一场关于人生巨变的命运交响,跨越24年的纪实蒙太奇:
《白马姐妹》里,大姐在废墟上拆烟囱,20年前的她正在安装烟囱;三姐对着手机描眉画眼,1999年她拿铅笔对镜梳妆;二姐捡起广告看着曾经的自己,1999年的二姐正背着南瓜由远及近走来。
为了找回“古老的民歌”,张同道遍访附近村寨爷爷奶奶们全部,抢救了一批濒临消失的白马民歌。民歌是白马人的生活日常和生命哲学,正如酒歌唱的,“人活一辈子,又唱又跳一辈子,只有唱和跳的欢乐才属于我们的。生命如旅人,不唱不跳干啥?”
在白马人的生活里,“跳曹盖”不是表演,而是为家园祈福的仪式;“圆圆舞”不是展示,而是劳作后围炉共乐的日常;古老的歌谣更不是标本,是母亲哄睡孩子时的呢喃。
影片中最动人的场景,是山洪过后男人们扛着木料修路,女人们一边和泥砌墙,一边哼着祖辈传下的调子。当新寨落成,四姐妹穿上绣着云纹的传统服饰,戴着木质的曹盖面具跳起祈福舞,面具后的眼神里,有对祖先的敬畏,更有对未来的笃定。

张同道说,大姐伍音早既会用智能手机接旅游订单,又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濒临失传的《酒歌》,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,是文化生命力的验证,“让更多人看到非遗不在博物馆的陈列,非遗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”。
诚利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炒股平台 广州一老字号餐饮品牌门店全部停业,曾连续多年入选米其林指南
- 下一篇:没有了